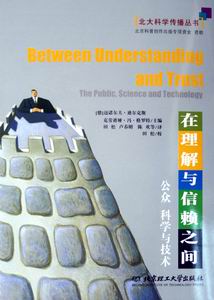 顾名思义,《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讨论的是公众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于是又涉及到理解与信赖的关系,当然,又需要讨论为什么要理解,怎样才算
顾名思义,《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讨论的是公众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于是又涉及到理解与信赖的关系,当然,又需要讨论为什么要理解,怎样才算
在本书中,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对象展开:一,公众理解科学;二,与之相关的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的调查。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公民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这两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1990年,李大光先后翻译了著名的博德默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和米勒的《美国1990年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状况调查报告》。米勒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以及美国的调查方式被引入到中国。中国科协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并从1992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但是,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所由产生的更深厚的背景,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被介绍过来,研究性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同样,我们的五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基本上是对美国、欧盟等地同类调查的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对于调查进行了改造,却并无自己的原初目的。对于国外此类调查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也相对薄弱。而本书则更进一步,它是国外学者对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与态度调查的反思和批判,更具前瞻性。这对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营养。
1995年底,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就欧洲公众对技术和科学发展的理解与评价进行了讨论。会后,迪尔克斯和冯・格罗特组织与会学者在参会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并于2000年出版。
本书从科学史、技术史、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媒体分析等各个角度,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研究历史、调查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既有理论论述,如第九章,耶利:《“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对科学本身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或者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思考;也有实证研究,如第六章,鲍尔:《作为文化指标的“媒体科学”:媒体分析的语境考察》,就媒体上科学的形象对英国报纸进行了抽样研究;还有案例分析,如第十三章,布奇:《一场舆论风暴,英国日报界中的“大爆炸理论”》,以一个物理事件在媒体中的传播以及所产生的公众影响为案例,进行了综合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同类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很好的借鉴。尤其是实证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中国科学传播学者针对中国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范例。
对于本书的核心概念“公众理解科学”,书中很多文章都对“公众”“理解”和“科学”这几个构成部分进行了彻底的解剖。如开篇第一章就是《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直接指向“为什么”的问题。另有如《理解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中的“公众”》《“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等。这种反思不仅表现在理论性的章节中,也表现在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因为这种反思已经成为各项专门研究的前提。
按照通常的观念,公众就是非专家、外行、无知者,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雨露滋润。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均一的公众概念,同时也预设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单向关系。然而,全知全能的专家是不存在的,一个领域的专家到了另一个领域,就成了门外汉,就成了公众。于是怎样定义公众,与“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就具有了相关性。而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又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某一社区具体的公众到底需要多少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科学,需要哪些科学。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遭到了质疑。菲尔特引用利维-乐布隆的话说:“在允许公民使用其投票权或者参加陪审团之前,我们并不需要他是一位宪法或刑法专家,甚至不需要他具有‘业余’知识水平。为什么在涉及技术与科学事务时我们要提出更多的要求?既然民主社会不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基本的法律(即文盲也有权利),为什么要求每个人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才能参与决策呢?”(第一章)
这个质疑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比如在近两年的怒江争坝事件中,建坝派对于环保人士常用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权参与决策。又如关于克隆和转基因等问题的争论中,也常常见到这样的言论:公众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不具备发言权。甚至还有人以公众不具备知识为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必标签,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要求公众无条件地信赖科学,只因为科学是真理,这种科学主义现在无疑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否公众越理解科学,就越会支持科学,也就是杜兰特所指出的,作为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缺省配置的“缺失模型”是否成立,本书当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论相当一致:不成立。缺失模型可以表述为“态度”和“知识”具有正相关。皮特斯(第十一章)根据德国某地公众对核能看法的研究中,发现态度与知识的关系是复杂的,而非单调的。有时表现为U形曲线,即知识掌握得越多的人,既有可能越支持核电站,也有可能越反对核电站。
那么,公众会为什么会信赖科学,又为什么会怀疑科学?在第九章中,耶利讨论了与科学相关的信赖与判断问题,讨论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色彩。耶利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不但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会存在信赖与判断,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信赖与判断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公众相信科学(家),并非公众理解了科学知识,而是因为科学家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公众之相信科学,与以往的公众之相信宗教,有着同样的理由。又由于科学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独特的利益集团,那么科学共同体连同科学知识遭到质疑也就是必然的。书中被多次引用的温内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调查,就常常被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反过来,公众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知的。本书中讨论了慢性病人的例子,很多病人对于自己的疾病有相当专业的理解,同时又具有医生所没有的亲身感受。这些感受和理解与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所差异,但也可以相互补充。从这个角度上说,公众与专家之间可以存在互动的双向关系。
关于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很多文章都强调了语境问题,即教科书上的科学、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问及的科学,都是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的科学。而公众在现实中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科学。比如本书第十章,索勒森等人对于挪威公众节能问题的研究表明,公众会有选择地掌握与节能有关的知识,并且会自己建构出一种模型来。这种模型在科学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来说更实用,更容易理解。那么,他们是否一定需要掌握那个“正确的”科学知识呢?
此外,即使从未受过科学教育的公众,只要能够生存,就必然会掌握使其能在那个地方生存的知识。这就是地方性知识问题。坎布里亚羊事件研究同样凸显了抽象的科学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无能和混乱,强调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人利用这个概念为传统文化辩护,帮助传统知识从科学知识那里争夺话语权。考虑泸沽湖边上生活的孩子,他们首先应该掌握的是本地的打鱼打猎种地的知识,熟悉本地的山水、动物和植物,会唱本地的山歌,知道祖辈流传的故事。而牛顿定律对于他的生活,显然没有具体的直接的帮助。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即使在地方性知识方面堪称专家,在接受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时,他的成绩甚至也会低于城市幼儿园的孩子。
由此可见,在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之中,还隐含着社会单向进化发展的理念: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代表进步,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谁就可以进入到先进的行列。这种理念与全球化的现代化理念相一致,但与文化多样性的文明理念相悖。当我们在人类文明模式的背景下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又会呈现出全新的层次。
在本书第一章,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菲尔特上溯到了科学的大众化活动,分析了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创建的平民大学。这些大学相当于工人夜校,也得到了开明资产阶级的资助。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这种科学大众化活动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工人掌握了科学,也就是掌握了先进的文化,并获得了进一步就业的机会。但是,菲尔特指出,在这里,资本家同样获得了利益。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合格的工人。按照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菲尔特引用罗克普洛的观点,指出了科学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假如认为现代社会是专家至上的,那么掌控日益复杂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就会在掌握它的人手中被改造成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意识和现实力量。按照这种逻辑,知识的转移并不一定对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有利。”
按照这种理解,科学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会成为一种力量,加速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有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工人,才有可能被剥削。科学大众化以及传统科普中隐含的线性社会发展观常常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如果所有人都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先进的行列,于是整个社会就进步了。这个幻觉对于个人是成立的,现实世界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些年名声很响的打工女皇,从一个打工妹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但是,这样的例子永远是个别的。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社会下层不可能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上一个阶层。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文明模式问题,不仅仅在理念层面考虑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矛盾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背景,即地球有限,单向的线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文明有一个限度,那么,科学和技术不能改变这个限度,反而会加速人类到达这个限度。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讨论。
由于本书是多位作者各自表述的一个集成,所以各个章节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不一致,非常有趣的是,本书的序言所表现的理念与大部分作者南辕北辙。序言作者,老一代科学传播学者诺尔―纽曼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恢复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赖”,而她认为本书会有利于实现这个愿望,这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总的来说,本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是一个颠覆。与之相关联的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理解与信赖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回答。本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不仅是很好的营养,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下面谈谈本书的翻译。首先对于某些具体翻译原则加以说明。
*鉴于中文“科技”一词具有歧义(严格来说,英文并无一词与之直接对应,书中有过techoscience一词,但只出现了一次。且此词在英文语境中极为生僻,远不如“科技”在中文语境中的平常),因而本书一般不使用这个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译为“科技”,而视上下文关系,译为“科学和技术”或者“科学与技术”,不做统一。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在汉语中看起来比较别扭的说法,如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而不说“公众理解科技”。
*本书中,understanding和attitude常常并列,常有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of? science之类的表述,严格来说,应该译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但是在长句中,会非常别扭,所以有时简化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和态度”,也会有“公众的科学理解”和“公众的科学态度”之类不大合乎中文习惯的表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以往常译为“科学普及”或者“科普”,但是由于“科普”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故译为“科学的大众化”。
*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主编,田松等译,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00元)
